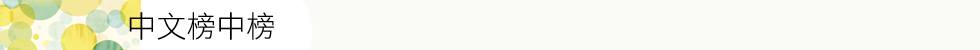紅色的負荷
洪星雅
當初是怎麼面對,人生的初潮?記憶猶新,那個愜意的午後。一次如廁中卻毫無預警地撞見,內褲上盛放的一朵鮮紅,似豔陽下傲然不群的玫瑰。我狼狽地像個做錯事的孩子,遠遠地拎著那條內褲奔向垃圾桶,再狠狠地埋入最底層,還不時探頭張望,確保沒有第三人在案發現場。那時約略明白是怎麼一回事,儘管故事中的小王子能全心呵護著他的摯愛,我卻還沒準備好迎接另一朵紅玫瑰。
那玫瑰起初羞赧,轉而愈發驕縱。她必定是位野獸派的大畫家,不肯拘泥於我提供的畫布,恣意潑灑、用色大膽,往往神來一筆,便又是一幅強烈、前衛的藝術作品,令我怵目驚心。偶爾她創作地過於忘我,我還得在寒風中解下外套緊繫腰間,以免公開展示觸犯了她的著作權。
妳說:「我的小女孩要變成女人了呵!」我晃著腦袋,長大,會是怎樣的滋味:是記得戴起市儈的面具?亦或遺忘單純的美好?每經歷一汩波流,流淌的不只是經血,也逐漸沖蝕了童年的共鳴:當我不願再嘗任何一口,斑斕色紙包裝的彩色糖果;當我開始質疑童話的幸福結局,只是不負責任的收尾。才赫然驚覺,改變的不只是跨下的潮汐週期,亦或未經耕耘田下地擅自萌發。還有什麼變化了呢?我不肯多想。
傳說月盈時分,狼人會身不由己地變成一匹嗜血的狼;而每當上弦月升起,我的理智也化作一頭難以控制的野獸、被「痛苦」狙擊的獵物。腹內強烈地衝撞,組織裡慌亂地逃竄,欲脫離軀體、欲掙脫束縛,每個毛細孔都在鼓譟咆哮。最終依舊徒勞,皮膚被一寸寸攻堅,成為「痛苦」的俘虜,咀嚼我的尊嚴、啃食我的意志。我只能等待,待它舔嘴咂舌之際,施捨我氣猶若絲的喘息,這是下次獵捕前的小小寬容。
我問:哪個傻瓜想當女人?
妳告訴我,來自紅色的喜悅。
妳抹上朱唇、撩起緋裙、踩破紅瓦;在眾人的祝福中舉杯,在彼此的指尖套上誓言。那天夜裡,妳與爸爸共享一顆紅艷艷的蘋果,在那貼有赤焰「囍」字的木門內,轟轟烈烈。我與妳的連結,墜落成一顆受精卵,透過一條堅韌的臍帶,仿如妳與爸爸繫著的那條,密不可分的紅線。妳以九個月的時間娓娓道出,妳深深的期盼,隨著腹部規律地脈動,一起一落,伴我成長茁壯。妳以溫柔負載我的重量,妳將生命注滿我的血液。
大規模的湧動、大規模的紅。用力收縮,我的迫不及待;用力收縮,妳的痛不欲生。等待地清脆地第一聲啼哭,這是妳最勇敢也最驕傲的時刻。朱緋瓦紅艷囍血,妳說那是一種授與母親的,專屬的紅色喜悅。親愛的妳,為我燒紅額頭而疼惜的眼淚、為我滿江紅成績而慍怒的雙眉、為我熱情似火地擁抱而出現的酒窩。未來我也會與我的孩子,共同分享這些紅色的美好,以一個母親的角色!
木門上的「囍」字,被時光曬褪成一種等待的顏色,等待傳承的顏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