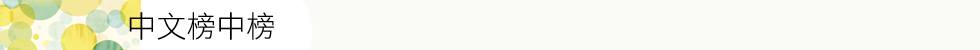再燃一把野火
陳郁文
《野火集》出版至今,已有三十餘年了,但這把火仍在燒。
一九八四年,《野火集》的第一篇文章〈中國人,你為甚麼不生氣?〉終於刊登在中國時報的專欄裡,它的出現或許並不是那麼的令人意外,當時人民正處於一個尷尬時期,生活上、思想上的剛開放,即使人們有想反抗的想法,卻也只能像難產而死的嬰兒,胎死腹中。犀利批判的字眼,毫不遮掩的銳利筆鋒,一字一句都似乎揭櫫著一個見不得人的醜陋事實,對當時的人民和政府無不是一個當頭棒喝。對這病態許久的社會而言,當時這篇文章的出現就像是一隻未燃的火柴,早已潛在的具有殺傷力,而龍應台就是那個無心的女孩給了它火苗,一燒就成了那燎原的星星之火,也成了推動台灣進入一個全新思想的野火。我們都知道它的出現是偶然,卻也是一個必然,對當時的社會而言。
從本書的第一篇〈中國人,你為什麼不生氣〉起到最後一篇收錄的〈容忍我的火把〉,每一短篇文的字裡行間,其實我們都足以看見龍應台對台灣的憂心忡忡,擔心台灣就這樣活在自己框設出的美好假象裡,但不過是個粉飾太平的面具罷了。只是她用了火辣辣的字眼去闡述她的親眼所見,用毫不拐彎抹角的生活案例去說明台灣人悶不吭聲的惡習。在〈生氣,沒有用嗎?〉一文中提及了黑心亂排汙水的工廠,隨意屠殺稀有動物的商人等等好多令人氣憤的事件,但大多數人卻只是在街頭三姑六婆的說著聽著也就罷了。當時台灣人的懦弱和屈服程度真是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,作者也毫不客氣的對事不對人在文中著實的抨擊與批判時事一番,彷彿給了一記深深的巴掌,要當時的人不要再做「沉默的大多數」,還有到底「要糟糕到什麼程度你才會大吃一驚?」。然而在〈生了梅毒的母親〉文中彷彿暗示著台灣就是那生了梅毒的母親,但至少它還沒有死去,就有痊癒的希望。作者在其中似乎刻意留下伏筆,她說:「我既不願遺棄她,就必須正視她的病毒,站起來洗清她發爛發臭的皮膚。」引出了我們是台灣人,我們就有責任去讓這個家、這個母親再活過來。如要說的再準確一些,那不是一個責任而是「義務」。
真的讓我心中亦燃起那把熊熊野火的莫過是〈幼稚園大學〉、〈不會鬧事的一代〉、〈機器人中學〉等等有關教育的文篇。大學生早就已經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,只留下盲目地追隨權威的通病罷了。如果要說大學生是那畸形教育體制下的受害者,那麼我們便可有罪證確鑿的證據去指出,那台上的教育者就是加害者。我們習慣去接受一個給定的最佳答案,在潛移默化中,早已習慣這種填鴨式的教育方式,不僅成了一種考試工具人,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我們逐漸地不去思考更多相關的面向,就像個機器人,一味的追求解答,過程中的「為什麼」根本不會有人去在乎!最終,我們活在一個只要求結果的荒謬教育體制下,繼續沉淪的躲在備受呵護的幼稚園大學裡。在這幾篇的文章中都有一個共通點,很多話都終將只是淪於口號喊喊而已。希望學生能明辨是非、擇善固執、見義勇為、當仁不讓,公民課說得口沫橫飛,但反觀現實,學校卻對這些挺身而出的學生總有個斬釘截鐵的官方統一說法:「去讀你的書,不要多管閒事,誰鬧事誰就記過。」你看,他們正在實踐自己的基本權利,但教育體制卻一點也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!然而慢慢地也會對這體制失去信心,更糟的甚至已經放棄台灣這個家了。逐漸的他們會覺得自己這樣的義無反顧和正義感,在這社會中是根本不需要具備的能力,也不容許存在。再回頭看看〈不會鬧事的一代〉文篇題目,饒是諷刺。就像一根針,紮紮實實的刺在我身上,沒有痛的感覺而是一種麻痺,對於這體制的麻痺,因為我們就是那群,被訓練成不會鬧事的「乖」學生。
《野火集》已出版三十餘年,但卻還是一直延燒的原因,就是這些弊病至今仍然在中國人的血液裡緩緩地流竄著。一把由龍應台點起的野火,燃起了中國人的認知進步,燃起了改變這病態許久的社會風氣。有時候我們的確需要當頭棒喝,去告訴我們自己到底有多麼可笑。龍應台在紀念版序裡有提到「新的野火,從哪裡開始?」對於現代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也就是我們而言,沒有政治的迫害,沒有高壓權威統治的無奈,也就沒有所謂再燃起一把新野火的必要了嗎?文中提及,現在企業對員工的踐踏、民主中的多數暴力、新聞媒體的作假和壟斷,每個時代,都有一個重新燃起野火的理由,只是,只是這把野火該怎麼燃起,又該從何燃起?
得知學校舉辦此活動,想想自高中畢業早已許久沒有提起筆好好地寫下一篇讀後感想,更正確來說應該是在電腦前花了好些時間敲打出這一篇讀後感想。其實好久之前就一直想親自見證一下這本書的厲害,終於,趁著這個機會把《野火集》這本歷久彌新的經典讀了一次,有種相見恨晚之感。書末,余光中教授曾以「龍捲風」來形容龍應台,即使台灣社會和中華文化裡,仍然有許多的頑固弊病是怎麼燒也燒不盡,但只要相信風夠強,野火仍旺,那麼頑固如野草的陋規惡習即使不能完全消滅,至少也不可能肆無忌憚的長得滿山都是。